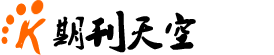“我思”之“思”———从“媒介环境论”角度对西方音乐理性化的反思
发布时间:2021-10-1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西方音乐的发展遵循着理性化特征,这与西方人长期以来尊重和崇尚的理性思维方式不无关联。本文尝试站在媒介环境学理论的角度,从印刷机、时钟、字母文字等人类媒介技术的发明探寻它们与理性思维产生的关联,并尝试反思人类思维、媒介技术以及伴随着技术
摘要:西方音乐的发展遵循着“理性化”特征,这与西方人长期以来尊重和崇尚的理性思维方式不无关联。本文尝试站在“媒介环境学”理论的角度,从印刷机、时钟、字母文字等人类媒介技术的发明探寻它们与理性思维产生的关联,并尝试反思人类思维、媒介技术以及伴随着技术发展的音乐艺术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音乐理性化印刷机时钟字母文字
缘起:由“媒介环境论”引发的“我思”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理性思维方式有着悠久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理性”便已成为西方人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精神内质。人们运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不断地试图寻求各种“确定性”,并为自身和自然立法;人们将认知的外部世界现象化繁为简:用一个公式、定理、概念来理解事物的规律,以便更准确和精细地认识它们的本质。当然,西方音乐也是理性思维传统下的产物。回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无论西方音乐的理论、记谱法,还是作曲技法与和声体系,都能找到“理性”精神的影子。正如汉斯·亨利希·艾格布雷特(HansHeinrichEggebrecht)、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和其主导原则是“理性”。如果我们说理性之思(“我思”)是西方人长期以来培养的思维习惯,那么西方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音乐的理性化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生根的……我们不妨围绕西方音乐文化展开“我思”之思。
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传播学的媒介理论给予笔者很大启发。
信息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学领域中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它是夹在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用以承载信息的工具和渠道。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简单的方式表现为:传播者通过某种媒介渠道将信息传播给接受者,并通过某种媒介渠道接收到后者的反馈。西方对于信息传播媒介的研究,大致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研究成果来自于美国经验学派,他们主要关注通过媒介渠道所输送的内容,对信息接受者的影响。而在欧洲大陆兴起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把研究的矛头指向了大众传播媒介。他们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抨击大众媒介作为资本主义传播手段,对大众进行奴化引导。
除了以上提及的媒介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一个新的媒介学派在20世纪中叶悄然诞生。这一学派很少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媒介承载的内容以及它们对受众的短期影响上,而真正关注“媒介技术本身”。他们认为媒介虽然是人类创造的,用以承载信息的工具,但它构成一个“环境”,我们仅仅是生活在它所构筑的环境之中。其中,我们的行动、思维无不受到媒介作用的影响。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首次公开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他给“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任务界定为:“把媒介当作环境的研究”。他指出:媒介环境学是研究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能力,以及感觉和价值观的;并且我们与媒介的互动是如何有利于或者阻碍我们生存的。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等人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
从“媒介环境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来看,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塑造人类思维、建构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笔者尝试顺着这一学派对媒介的研究逻辑和成果,找寻各种媒介技术与西方音乐理性化进程的联系。
一、印刷机对世俗精神的催生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尝试解释和分析西方人在包括音乐行为中的理性思维成因,他认为西方人理性行为方式,和16世纪宗教改革以及新教伦理相关。他的观点受到了美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批评,她直言不讳地说:“韦伯关心的发展变化(含理性与科学)正是在印刷术这种新媒介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但他的著作给予印刷术的地位却很不引人注目。”在宗教改革的背后,爱森斯坦看见了印刷媒介的推动力量,认为印刷媒介技术发明以后,西方文化里的理性化和系统组织化逐渐实现,进而把西方理性的产生和实践着眼于人类所发明的媒介技术
我们知道,西方的记谱法产生于公元90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的修道院中的僧侣们,创造了一种能够提示人们音乐旋律走向的纽姆谱。进入第一个千年以后,圭多(Guido)发明了能够记录音高的线谱。不过这些乐谱都以费时费力的手抄形式记写,制作成本高、效率低,成品大都归贵族和教会所有。15世纪中叶,德国商人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音乐乐谱的印刷和出版也因此方兴未艾。根据德裔美国音乐学家阿尔夫莱德·爱因斯坦(AlfredEinstein)的介绍,在古登堡印刷首次尝试的25年后,德国和意大利印刷技师印刷出版了祈祷书。乐谱的印刷由弗索姆布隆(Fossombrone)的奥塔维亚诺·德·佩特鲁奇(OttavianodeiPetrucci)完成,威尼斯成为复调音乐印刷和出版的中心。
正如书籍印刷在欧洲文化史上的作用,音乐印刷的发明在音乐史上也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时间维度看,印刷机对于音乐文本的复制功能有益于书本和乐谱文献在时间上的保存,这保证了大量手抄文献,不至于因为社会动荡而瞬间毁于一旦;从空间维度看,印刷机伴随着纸张的普及,使得书籍和乐谱便于运输和普及。
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刷机的发明,无论是德文版的《圣经》还是乐谱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售出,并在大众中得以普及,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圣歌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广阔市场。这种“摧毁”不仅把长期垄断于教会对文本的解释权转移到了每一个普通人手里,也大大地削弱了教会对人性长期以来的打压和遏制,世俗人文精神因此觉醒与发展起来。有学者提及到“基督教音乐长期独秀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在中世纪备受压制的欧洲世俗音乐的传播日趋发达,并因其传播之影响而终至形成与宗教音乐分庭抗礼的局面。”正是因为这样,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我思”在长期宗教信仰的黑暗中,绽放出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我在”从神权神授的尴尬地位中摆脱出来,孕育了独立和个体的地位。印刷技术加速了音乐家们摆脱宗教意识和传统束缚进程,作为“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严酷的宗教环境中萌发出来,以“我思”和“我在”的独立意识和身份投入到音乐实践活动之中,并按照自我的审美意趣和音乐自身的法则进行音乐创作,当时作曲家作品的成名以及其名望的上升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这是西方人独立思考、用理性的方式面对音乐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机械时钟与音乐“有量”节奏观念
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并不认为爱森斯坦所关注的印刷媒介就是西方文明理性化的源头。在他的观念和笔下,西方理性精神的诞生足足提前了几个世纪。芒福德察觉到时钟以及此后发明的机械钟表对西方文明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作用。
7世纪时,修道院的僧侣们“即使是在难以判断时间的夜晚、阴天,也必须致力于保持统一的作息习惯,他们需要在天黑时出现,在合适的时间中诵咏合适的祈祷文。”因此“本笃会把修士祷告的次数增加到一日7次。教皇萨比尼埃纳斯(Sabinianus)的圣喻就规定,修道院一天24小时要敲钟7次。敲钟的时间就成为‘祷告时间’,用以记录祷告次数,确保有规律的作息。”芒福德认为这种计时的方式要求修道院的僧侣们养成按时祈祷和生活的习惯,目的是让宗教生活与世俗的变化无常相隔绝。在1300年前后,时钟第一次出现在法国和德国。同时期,西方人发明了机械钟表,并对时间做出了刻度的划分。此后,城市中数不尽的钟塔揭开了西方文化历史中的定量(quantification)时期,培养了文艺复兴的人们协调一致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总之,人不自觉地被推到了由机械时钟所构筑的整齐划一的思维活动中,这成为西方的理性精神发展的推动力。
做到行为的协调统一,同样也是基督教音乐仪式和礼拜活动的基本要求。早在公元6世纪时,本笃会的规章中就明确规定,“唱诗班咏唱诗篇应该就像只有一个人,任何歌手不得唱得比其他人更快或更响。”可是,早期基督教圣咏音乐并没有明确的节奏,单纯根据文本的节律仅仅能够满足单声音乐齐唱的要求,而面对多声音乐,僧侣们在歌唱时便很难做到预想的统一。有西方学者这样论述当时的歌唱情景:“如果我们试图齐唱,同时开始、歌唱和停止都不困难。如果我们试图唱几个相对独立旋律声部的复调,开始很简单,但是立即就会陷入混乱。我们需要节奏和实践上的引领;我们需要知道歌唱进行的速度……”因此,一种极力精确和量化的记谱方式便呼之欲出。13世纪,科隆的弗朗科在其著作《有量音乐的艺术》中,用独立的音符形状记录节奏,实现了对于音乐节奏的精准量化。笔者看来这绝非偶然,恰在当时,机械时钟赋予人们的时间观念推动他们产生了对于时间(音乐中的时值)有量化的兴趣,并对音乐的节奏记录进行有意识地创造。和时钟一样,人们通过“有量”记谱的方式将每个音符的时间视为一个单元,并将这个单元的时间间隔量化和可视化。有材料显示,13—14世纪,音乐理论家们认为:“时间有单元,基本的单元被成为‘拍’(tempus),那么一拍有多长呢?1300年左右,格罗奇的约翰内斯(JohannesdeGrocheo)说:‘一拍是最小音高和最小音符被完全呈现或者能够被呈现的时间间隔。’(intervalinwhichthesmallestpitchorsmallestnoteisfullypresentedorcanbepresented.)”由此,人们音乐实践活动便有了“有量”可依的标准,克服了他们在面对复调音乐歌唱难以统一的窘困。
无论是时钟还是音乐的有量记谱方式,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有学者说:“农业社会心理时间观形成的影响主要来自人们的物理生存环境,自然界的变化及其规律是心理时间观形成的主要参照体系。”与其说古代原始人对于时间有种观念和概念,倒不如说他们对自身生活的绵延状态有一种体悟。时间本身和人合为一体,不分表里,它内化于人的身体的感觉之中。而有量化的媒介把人们限定在了外化于自己身体的时间刻度中,人不再根据自己的身体和感官去体悟时间,相反,时间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客观之物。它作为一种被人理性抽象的对象,甚至控制着人的身体。麦克卢汉认为:“(钟表)不靠个人独特的经验计量时间,而是用抽象的统一单位来计量时间,这种方式计量的时间慢慢渗透进了一切感知生活。”正如前文所言,早期基督教圣咏音乐并没有明显的节奏,僧侣们在音节式的音乐吟唱中并不是根据准确的有量时值,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观念,而是根据经文的句读(或者说凭借自身的呼吸)进行断句,换句话说,僧侣们评判音乐的节律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体悟。然而有量化的乐谱产生之后,它就像一台精准而巧妙的时钟,以可视化的方式准确地告知人们每个音符的时间单元,使人按照“外在于人”的时间观念处理每一个音符的节奏。从此,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不再按照自身的感觉和体悟,而必须遵循每个音符的时值。
相关知识推荐:论文发表期刊真假辨别方法
总之,作为人类文明的媒介技术,没有任何一种能像时钟一样把人们卷入一个统一协调的行动之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像时钟一样,把人们从对自然的依赖和感性体验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精确计数和数量切分的世界。在音乐文化的进程中,乐谱起着和机械时钟一样的作用。
三、字母文字对音乐的符号化记录
还有一群传播学者并不能同意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比如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就在论著中提到:“芒福德没有注意拼音字母表的影响;使时间的视觉切分和统一切分成为可能的,正是拼音字母表。事实上,他没有意识到拼音字母表是西方机械主义之源。”麦克卢汉把西方理性思维的动因又向前推了几个世纪,给出的答案是西方的字母文字。真正直面以上问题的是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和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J.Ong)。他们一致认为在口语文化中,人们凭借记忆能力无法进行抽象分类、形式逻辑推理,“聚合式的、情景式的、重视冗余的”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不从事任何“研究”,而字母文字作为一种可视的、可记录的代码系统对人们的思维能力进行了重构,促进了人们抽象的、形式逻辑的理性思维。
古希腊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字母文字的普及和内化,无疑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包括音乐在内的“口述”文化逐渐转型为“文本记录”的文化。史诗曾经是古希腊辉煌而灿烂的文化象征。在相当长的岁月中,音乐伴随着巨幅长篇的史诗在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口头吟唱中流传,人们并不愿运用文字和我们所谓的“乐谱”将它们记录下来,而是希冀于通过记忆加以保留。虽然诗歌通过诗人们的口头吟唱会发生各种变异,然而它仍被看作是诗人感性幻想的产物,甚至是出自缪斯所赋予的神启,这种人类活动非理性的产品最初并不被视为“艺术”(等同于“技术”)。当然,音乐最终成为了艺术———“自由的艺术”,一门理性参与的实践活动,其程度与数学家的活动所表现的情形相仿。有西方学者这样论述:“对希腊人来说,一切都是算计。例如,他们计算出八度音、四度音和五度音是和谐音,而三度音和六度音则不是。他们是否真的喜欢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似乎有点可疑,一个真正的希腊人不值得依靠自己的自然感觉,他觉得自己注定要在数学的神圣事业中受尽折磨。”显然,这是古希腊人对于“音乐”这门“艺术”态度的变化,更是他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由感性体验到理性思维的改变。这个过程和字母文字记录方式的产生不无关联。
首先,在口头传播形态中,信息传承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人发出声响的一瞬间,音乐或(诗歌)言语即生即灭,音乐从诞生伊始便与音乐实践的主体“融为一体”,甚至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可谓人在哪,声音便到哪。因此诗人完全投入到对于音乐的感性体验之中,并进入“物我同一”的“无我之境”的状态。哈弗洛克认为在口语文化传统中,“我”很难从自身的感性体验中抽离出来,因此也就无法形成“自我”意识,并站在“我”的角度把活动的对象当作异己的“客体”,对其进行理性的抽象和分析。然而,正如翁所言:“文字把知识持有人和已知对象分离开来,使人的内省日益清晰,打开了心灵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通过书写记录(尤其是西方字母文字)手段,曾经口语发生中瞬息万变和偶然性的声音“凝固”下来,成为一个脱离于人们身体的,相对于自身(主体)的客体存在,这也就造就了人们将其视为“客体”对象,并将自己视为面对“客体”的主体,“主、客”二分的对立便由此产生了。这样,由于文字记录手段的出现,诗歌被作为人们理性思考和运算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通过书写记录,人们从口头文化中依赖“耳朵”的“声音世界”,进入了依赖“眼睛”的“视觉世界”,这个过程打破了人们感官的平衡,尤其“延伸”了“视觉”感官功能。古希腊时,idea(观念、理念)和拉丁文video派生出相同的词根,它们和“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沃尔特·翁看来,柏拉图的理念(idea)世界正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看”的世界,它排斥了口语文化中热烈的、人与人直接互动的感性直观,塑造了凌驾于生命的理性抽象世界。如果说黑暗通常代表了愚昧、无知、野蛮和非理性;光明则表征了知识、理性、科学和文明,这里的黑暗就是人们无法被人所看见的状态,光明则是照亮黑暗,成为看得见的东西。而这一过程也就是通过人们的眼睛去“看”的过程,更进一步说也就是一个“去蔽”和“启蒙”(theenlightenment)的过程,即“把某种事物从不可见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使之处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可以看见的东西……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的转变。”那么,通过“看”的书写方式,人们被引向了理性之路,人们的眼睛就像一座灯塔,向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投射出“去蔽”之光。对此,西方学者J.C.卡罗瑟斯(J.C.Carothers)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论据,他对未掌握文字的土著人和掌握文字的西方人加以观察和比较,他发现非洲人生活在声音的世界中,他们不把眼睛当做接收信息的器官,而西方文字使得西欧人迈入一个视觉的世界中,不仅失去了听觉世界的动态特征,还形成了机械的理性逻辑。——论文作者: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