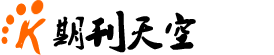裁判文书援引宪法的“能”与“不能”——“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的法理解读
发布时间:2021-07-09所属分类:法律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内容摘要】 自五四宪法施行以来,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来加以回应和解决。按照当前的司法政策,裁判文书能在裁判说理中援引宪法,但不能在裁判依据中援引宪法。此即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的司法政策。在裁判依
【内容摘要】 自“五四宪法”施行以来,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来加以回应和解决。按照当前的司法政策,裁判文书能在“裁判说理”中援引宪法,但不能在“裁判依据”中援引宪法。此即“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的司法政策。在“裁判依据”中不能援引宪法,主要是基于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特殊性及防范宪制风险的政治考虑。在“裁判说理”中能援引宪法,既为“宪法间接适用新说”所支持,又为全面实施宪法和司法理性化所要求。实证研究表明,“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基本能满足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裁判说理”中援引宪法的司法实践,必然要求承认人民法院拥有法律方法层面的宪法文本解释权。

【关键词】 裁判文书 司法政策 裁判说理 裁判依据 宪法适用
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能否援引宪法,关系到我国宪法的实施和适用,也涉及法律渊源的性质,因此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五四宪法”施行以来,关于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以及如何援引宪法的问题,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来加以回答和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八二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宪法适用学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治理法治化,关于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的司法政策,经历了从“不宜援引宪法”的旧政策到“裁判说理”中能援引宪法但“裁判依据”中不能援引宪法的新政策之变迁。当前所实行的此项关于宪法援引的新政策,可被称为“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此项司法政策主要建立在对裁判文书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裁判文书的正文在形式结构上可区分为“案件事实”“裁判说理”“裁判依据”“裁判主文”等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法,“裁判说理”部分是位于“事实”部分之后、“裁判依据”部分之前的“理由”部分;“裁判依据”部分则位于“理由”部分之后和“裁判主文”之前,也就是裁判文书样式中“判决/裁定如下”之前的“依照/依据……”部分。〔1〕在“裁判文书样式”的语境中,“裁判依据”被严格地理解为“裁判结论所依据的最终的规范基础”,〔2〕也即可直接涵摄已确定的法律事实之规范,从而区别于说明和论证何以选择适用该规范的“裁判说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关于裁判文书制作技术的司法政策,但实际上却关系到我国宪法和法治的实践发展,且与我国宪法和法治的理论发展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这项司法政策并非是单纯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是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互影响以及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紧密互动的产物,兼具经验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法律性,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法治实践需要法学理论的回应和反思,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本文以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为问题意识,以“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为考察对象,探究此项司法政策的来源和性质、宪制基础和法理依据、实践效果及其法理意蕴。
一、“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的来源和性质
“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法院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及“如何援引宪法”这一问题所确定的一项司法政策。此项政策的明确表达,出自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该文件在正文第(七)部分的“裁判依据”中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3《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是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的形式发布的,因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而仅仅是法院系统内部有关裁判文书制作技术的政策性文件。〔4〕因此,该司法文件中援引宪法作为说理论证和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区分性规定,应被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以及如何援引宪法的一项司法政策。此项司法政策包含着一个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技术性规则:人民法院“能”在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部分援引宪法,但“不能”在裁判文书的裁判依据部分援引宪法。
实际上,2016年“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的正式出台,是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的超越。后者是司法解释文件,〔5〕其第1条指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吴兆祥法官专门撰文解释说:这一规定是指“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范围限于法律、法规等范围,不包括宪法在内”。〔6〕该司法解释文件第6条又规定:“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其中所包含的“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这一限定条件,说明“宪法”不在这一条文所说的规范性文件之内,因为法院无权对宪法进行审查认定,宪法的合法性也无需法院来加以宣示。可见,在2009年这一文件出台时,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可能,但对于宪法能否被援引用于裁判说理这一问题,尚未给出明确的回答。2016年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则明确给出了肯定性回答,至少就民事裁判文书来说是如此。
然而,就刑事裁判文书来说,政策上允许法院援引宪法用于裁判说理的可能性似乎也不是没有。在2012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废止1979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八批)的决定》(法释〔2012〕13号)中提到:废止195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所持的理由是“定罪科刑以刑法为依据,复函不再适用”。废止理由中说到的“定罪科刑”与《复函》中言及的“论罪科刑”,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该司法文件的制定者只是强调刑事裁判文书必须以刑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并不否定法院援引宪法用于裁判说理。
而且,“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出台之前,如下文所将论及的那样,在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上,作为“裁判说理”和作为“裁判依据”的区分论,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7〕进而影响到具体的司法实践。2016年年初,一份民事判决书曾引发社会媒体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在“说理论证”部分引用了宪法上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文,并在其后用括号标注道:“此处引用宪法并非作为裁判依据而仅用于判决说理论证。”〔8〕暂不论该裁判文书对宪法的援引是否一定妥当,但该援引行为本身就表明:作为“裁判说理”与作为“裁判依据”的区分论,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者说,“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的二分政策,虽然尚未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肯认,但是已经获得审判系统的广泛认可,以至于体现在基层的司法实践之中。
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第13项提到:“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该《指导意见》虽未明确提及宪法,但不可否认,宪法上的规定既可以作为体系解释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凝聚着“公理”“法理”的规范性论据(表现为各种宪法原则〔9〕)用于裁判的说理论证。〔10〕所以,无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情形下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不仅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而且为目前的司法政策所鼓励。
相关知识推荐:国外法学类期刊怎么选
然而,也有学者曾对该项司法政策的合宪性提出质疑,认为2016年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所阐明的法院裁判依据部分,实际上是在对《宪法》第131条中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的“法律”的内涵进行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无权对宪法进行解释,因此该项司法政策就存在合宪性问题。在质疑者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宪法》第131条中的“法律”一词进行宪法解释。〔11〕
的确,该司法政策的出台,是有可能涉及对《宪法》第131条中“法律”一词的解释,但是,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任何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都难以避免对宪法作解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宪法的解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者的经常工作。”〔12〕而法院在审判中对宪法的解释也被认为是法院的固有权力:“对法律作出解释无可置疑地是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和责任。宪法不是道德说教,它是具有法律力量的。实际上,它是根本法。”〔13〕要维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就必须通过解释来落实作为宪法规范的根本规则和根本原则。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包括法院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都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而宪法的实施必须离不开对宪法条文的理解和解释。
自然,我国没有在宪法中确立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因而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在法律效力上并没有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的解释那样具有权威性。然而,法律解释可以分为“权威性解释”和“实践性解释”,前者指“解释权威进行的解释活动”,后者指其他主体“为了明确法律条文的含义(以便于从事遵守、执行、适用或其他法律实践活动)而进行的解释活动”。〔14〕同理,我们不能以存在权威性的宪法解释主体为由而否定其他主体从事实践性的宪法解释。所以,“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可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目前的中国宪法适用体制上对《宪法》第131条的实践性解释,不存在权限上的合宪性问题。〔15〕当然,“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在实体上是否合宪,是否具有法理上的依据,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讨论。
二、“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的宪制基础和法理依据
“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的形成,与我国宪制实践和理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二分政策”中不能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要求,又是之前“不宜援引宪法”的旧司法政策的延续。因此,对“二分政策”的宪制基础和法理依据之揭示,既需要对旧司法政策及其背后的宪制基础和宪法观念作出分析,也需要对旧政策为何升级至“二分政策”的过程和原因做一番探究。
(一)我国宪法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宪法观念
“裁判说理”与“裁判依据”二分政策中不能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要求,首先源于我国宪法的政治性质及政治宪法的观念。基于依法裁判的传统法治理念,宪法上的政治原则和要求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后方能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这也反映在“不宜援引宪法”的旧司法政策的法理依据中。
关于旧司法政策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298号)中,该《复函》是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文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显而易见,在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上,旧司法政策并未有意识地区分作为裁判说理的援引和作为裁判依据的援引,而是笼统地持否定态度。而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该政策背后有一种将宪法视为“母法”的宪法观:所谓“母法”,其与作为“子法”的普通法律相对,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立法原则,使国家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16〕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观,与作为“母法”的宪法观颇为接近,同样强调宪法作为立法的基础。正如斯大林在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17〕如果将立法视为实现特定目的之政治活动,那么重在为立法提供基础和指引的宪法,必然是政治性质主导的宪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家们看来,“五四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政治宪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18〕所以,“五四宪法”呈现出很强的纲领性特征。一方面,宪法被认为是革命成果的记录和“历史经验的总结”。〔19〕《宪法》序言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历史经验的叙述“不只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提炼基本结论,以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导”。〔20〕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21〕为此,有学者认为,“五四宪法”“显然被当作一份理论文献”,仅被视为行动指南,而非教义或信条。〔22〕另一方面,“五四宪法”被认为是过渡时期的施政方针和政治纲领。所以,毛泽东曾指出:“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23〕刘少奇也曾言及此一制宪目的:“我们有完全的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制定一个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肯定下来。”〔24〕总之,“五四宪法”被认为是立法工作的基础或者政治行动的纲领,而不是与普通法律一样可通过司法予以适用的规范。〔25〕正是在这种政治宪法观念的支配下,人民法院“不能”依据宪法裁判,而必须依据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来进行审理和裁决。换言之,人民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有学者将此种否定宪法直接适用的学说称为宪法间接适用说:“间接适用是指宪法先由代表机关转化为更具体的规范(该转化是直接适用),再由相应机关通过适用此具体规范来适用宪法。”〔26〕然而,这里的“适用”概念是广义上的,也就是把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的立法行为也算作“适用”的一种(直接适用),而把法院依法审判的行为算作“适用”的另一种(间接适用)方式。
由于“五四宪法”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部“很好”的宪法,因此,“八二宪法”草案的拟订就直接以“五四宪法”为主要参考,并且明确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并非新的创造,而是新时期对既往政治原则的概括和提炼。“八二宪法”的制定也被认为是“恢复四项基本原则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步骤。〔27〕正是因为“八二宪法”与“五四宪法”之间的连续性,“八二宪法”制定后,前述政治宪法观念和宪法间接适用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裁判文书“不宜援引宪法”的司法政策也因此延续下来,并在198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问题的答复》中得以明确体现。《答复》指出:“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当事人双方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也可引用。”〔28〕同样,该《答复》未区分作为裁判依据的引用和作为裁判说理的引用,如果运用反面解释方法,宪法显然也被排除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和经济案件可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外。总之,“八二宪法”较之于“五四宪法”,乃至于其后三十余年的几次修订,虽然在法规范性质层面有所提升,〔29〕但不能说已超越了政治宪法的基本性质和观念,〔30〕因此也并未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论文作者:张卓明